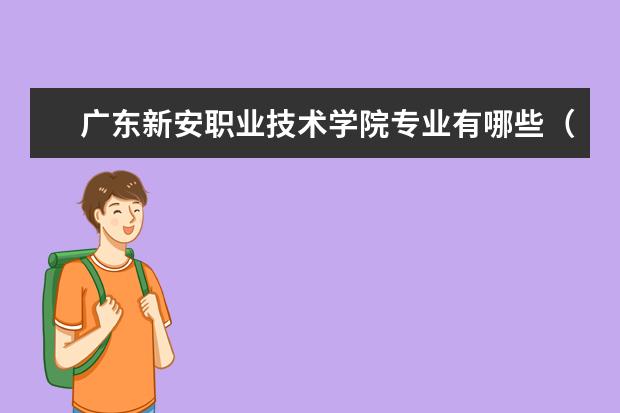最近经常有小伙伴私信询问佛学与哲学的区别是什么?相关的问题,今天,大学路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,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本文目录一览:

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是哪一所大学?
1. 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是
哈佛大学
。
2. 2018USNews世界大学排名如下:
拓展资料:
1. 哈佛大学简称哈佛,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市区剑桥市,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研究型大学,是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成员。截止2018年3月,这里走出了8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,157位诺贝尔奖得主(世界第一)、18位菲尔兹奖得主(世界第一)、14位图灵奖得主(世界第四)曾在此工作或学习,其在文学、医学、法学、商学等多个领域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广泛的影响力,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。
2. 哈佛同时也是美国本土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,其诞生于1636年,最早由马萨诸塞州殖民地立法机关创建,初名新市民学院,是为了纪念在成立初期给予学院慷慨支持的约翰·哈佛牧师。学校于1639年3月更名为哈佛学院。1780年,哈佛学院正式改称哈佛大学。截止2017年,学校有本科生6700余人,硕士及博士研究生15250余人。
3. 哈佛法学院(Harvard Law School)创立于1817年,虽然比大学部(Harvard College)建校(1636)晚几近两百年,仍是美国最古老的法学院。
佛学与哲学的区别是什么?
在近代中国佛教,比较深入阐述佛法、宗教、哲学三者的关系,首推太虚大师。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很多,对佛法与宗教关系的著作,有《我之宗教观》、《宗教观》、《宗教构成之原素》、《我之佛教观》、《佛学与科学及宗教之异同》、《无神论》、《破神执论》、《天神教之人界以上根据》、《佛教化的世界宗教学术观》、《中国需耶教与欧美需佛教》等,我们可以看出,他对佛法与宗教的关系及区别十分关注,而且思想十分丰富。
首先,他对宗教的定义、起因、本质、构成要素、差别等次及未来都有系统的阐述。对于宗教的定义,他在《我之宗教观》上说:
今且就流行之宗教一名,下一定义,现在所谓宗教,本之中国原来之语意,应可但称为教--如中国言儒、释、道三教等。教即宗教,故佛教及耶教等皆为宗教。而教皆有自心修证及教化他人者之两方面,个人自心修证之实际曰宗,而本之以教化他人者曰宗教。……则宗教者,有内心修证之经验为宗本而施设之教化也。〔17〕
太虚大师吸收了近代美国实用主义心理哲学家威廉·詹姆士从个人内心体验对宗教的理解,这样他不但把佛教、基督教和*是宗教,而且“即如中国孔、老,亦有其特殊之内心体验,断断乎非未尝修证人之见闻觉知所能征验者”,这实际上把儒家、道家也看作是宗教。〔18〕而且,他认为宗教与一般的哲学、科学不同在于“以其所施之教有超常之内心经验为宗本故”,这与美国的宗教经验学派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。
对于宗教起因,太虚大师归纳为四种:一、由偶感奇幻神秘之灵境,因为梦境、幻境及某种“心理变态”而引起的神奇“灵境”,这是“诸灵魂教”的产生原因;二、由造作者及主宰者之推想,因为宇宙万有如此繁密严整,于是便设想必有“唯一之主宰”,这种“假想”再同“内心灵感”联合起来,这是“耶、回、婆罗门等之天神教”的产生原因;三、由对于人世不满及图超登之满足,希望“除所苦而臻所乐”以“求超脱以遐登乎满足之域”,这是佛教的“大乘教及小乘教”产生的原因;四、由人生意欲无限价值永存之要求,“视人世如牢狱,感人生之空虚,於此须了解人生之真相——本来面目——究竟如何,此理不关於诸宗教及诸哲学,而大乘佛教亦由之而起——唐宗密原人论亦明此义。”这是大乘佛教的产生原因。〔19〕太虚大师的这四个起因,可以说都是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。
对于宗教本质,太虚大师归纳为四点:第一,自心信修所获之超常证验,这是通过修持,而获得“超过通常人见闻觉知之上而自得其不可思议之证验”,如佛教的“三昧”、耶教的“圣灵感通”,这些都不是“学理上研究之可得”的“自心信修”的不可思议之证验;第二,开示超常证验及趋入门路之教训,也就是“必宗本其自心之超常证验以开化他人,著为教训,令皆悟入”;第三,表现超常证验或方便应化灵迹,“方便应化”以“表现超常证验”,或“种种灵奇神通”而使人钦慕;第四,引导及规范其徒众之仪制,就是为了“引导”教徒信众而制定的各种“相好庄严之仪式”以及“应守之规范”。另外,他还指出宗教有“为损或为益于人心世道之旁效”,这就是多数宗教是有益于人世,另外还有“害人之邪教”。〔20〕从此,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宗教本质的认识,仅仅是宗教的一些特征,仅是心理上的,而忽视心理因素背后的更深层的社会因素。这当然也是因为他受了威廉·詹姆士心理哲学观念影响的结果。
对于宗教构成的要素,太虚大师在《宗教构成之原素》一文中也归纳为四点:第一,“超于平常理智”的“心灵上之非常经验”,这是各种宗教如基督教、*、佛教及中国的儒、道都有;第二,“大悲愿力”,因为“觉察宇宙万物与乎世界人类,皆可得达超出尘俗之非常灵知经验,以同享彻底之安宁快乐。但观世人皆未自臻此境,于是大悲哀悯之心生焉”;第三,“通达事理之知识”;第四,为适合时机之德行,即“适合时代需要之道德行为”。在这四种要素中,以“非常之灵知经验”最“切要”、最“根本”,而且“佛法於此非常灵知之经验,最有精当而不偏颇、严密而不疏懈之说明。要之,此非常灵知,乃为宗教经验,而通达其中事理以评判论断之者,则为宗教哲学。佛教之精华,即在于此!”〔21〕太虚大师的这四种要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,同时他强调“非常灵知之经验”,是受到心理哲学的影响;而且他强调佛教高于其他宗教,是因为佛教本身宗教哲学的精当、严密,这是确实的,当然这也是作为一名佛教大师的护教立场。
太虚大师还对各种宗教划分不同等次:一、鬼灵教,是“最低限度之宗教”,这种宗教“大多以祸福耸动于人,其奉行崇拜者,多为迷信盲从无知识之人”,“日本之多神教,中国之道教,及现时流行之同善社、道院等”就是属于鬼灵教;二、天神教,高过鬼灵教之上,“如印度有崇拜梵天之婆罗门教,耶教、*之信上帝真宰”,因为他们“推想宇宙万有有造作主宰者为唯一真神,而否认种种鬼灵者”也。三、自心教,这是“依自心信修所获之超常证验,认定惟是自心之心境,否认种种鬼灵及惟一无二能造作主宰宇宙万有的造作主宰者。”自心教又分为四种∶一、静虑教∶即重禅那,如宋明理学亦重静虑,“虽尚属人天教,已非仅有理论上推究之世间一切学说相比拟也”;二、存我教,如印度数论派与耆那教等,“依前静虑更加其哲学之理想,计以自我之独存为解脱,要将宇宙消归於无影无响,而神我遂得解脱而永久存在”;三、无我教,即佛教的小乘,否认其所存之我而主张无我;四、正觉教,即大乘佛教,“于宇宙万有世出世法,皆能正确了知其本来如是之真性实相,犹如大圆明镜清净光,更无无明障蔽。发起求此正觉之心,即无上菩提心;此心情与无情悉皆平等,惟须由众生而至成佛,乃成正觉而得圆满”。 〔22〕下面,我们将其文的表格列出:
┌鬼灵教
│天神教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人天教
宗教差等┤ ┌静虑教
│ │存我教————外道教
└自心教┤无我教 小乘
└正觉教 大乘 佛教
从太虚大师对宗教的分类,我们可以看出他的“宗教”概念十分宽泛,包括各种鬼神信仰、无神教及宋明理学。同时,他不仅将佛教(包含大乘和小乘)置于一切宗教之上,更将大乘置于小乘佛教之上。这反映出他并不认为佛教因与其他各种宗教有别而不属于宗教,而只是认为佛教,尤其是大乘佛教是最高的宗教。〔23〕但是,他将宋明理学归入静虑教,而又说“属人天教”,这有逻辑上的混乱。
太虚大师在佛法与宗教、哲学的关系上,他提出佛法是宗教而又不是宗教,是哲学又不是哲学。他在《甚么是佛学》一文中说:
佛学在文化上,占最高底地位,它究竟是哲学呢、宗教呢、科学呢?甲说是哲学,乙说是科学,丙说是宗教,议论纷纭,是皆不懂佛学而下武断的言论,为向来未决之悬案。就哲学之出发点说,或为宗教之演进,凭空想像的解释人生宇宙;或为科学的发达,根据“心理”“生理”或“物理”学来说明人生宇宙∶哲学虽与佛学同一说明人生宇宙,而实与佛学不同。佛学之出发点,由与修养所成圆觉的智慧,观人生宇宙万有真理了如指掌,为了悟他而有所说明;所以佛学虽可称哲学而又不同哲学。且佛学不过以解说为初步的工作,他的目的在实行所成的事实,如度一切众生皆成佛道,变娑婆秽土而为极乐是。如三*义能团结全国人心,领导国民革命,是有宗教之作用的;佛学的功用,在开人天眼目共趋觉路,亦自然有伟大的宗教团结力。但虽是宗教,却没有其他宗教所崇拜的神,或神话迷信,故又可说不是宗教。〔24〕
他将佛法置于一切宗教、哲学及科学之上,来佛法来统摄各种文化,他列表如下:
┌宗教—┬————文学—┐
佛学┤ ├—哲学├美术
└科学—┴————工艺—┘
关于佛法与哲学的关系,太虚大师在《论哲学》、《佛法是否哲学》、《西洋、中国、印度哲学的概观》、《佛法与哲学》、《唯物、唯心、唯生哲学与佛学》、《佛学与宗教哲学及科学哲学》等文中加以阐述,从而开掘佛教中的哲学理论,寻求佛教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长点。1928年,太虚大师访问英国时,在与罗素的一次会面中,太虚大师指出罗素的哲学,“颇多与佛学同点。”“若中立特体为各各独立存在之非因缘所生法,则近于佛学中小乘一切有部之实有法。若亦为因缘所生法,则近于大乘缘生性空之法。”〔25〕太虚大师认为佛法比一般哲学思想,无论是西方的、中国的,还是印度的,要优胜得多,他在《佛法与哲学》一文中说:
在哲学上,要知宇宙真相本体之出发点,与佛学之求正觉法界不无相同,但哲学家卒难确知宇宙之真相本体,或计之为一元、多元、无元等,思维筹度,遽执为当!不知此摸背言床、抚胸言地之徒,或差胜於捏尾言绳者之一筹,而所见较广则有之;然以此瞎子之所摸得者,较彼明眼人之亲见全象,活动自如,仍迥然不同也。何以故?皆不出错觉之一途故。〔26〕
太虚大师认为在探究“宇宙真相本体”的出发点上,一般哲学与佛学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,但是因为哲学家们的“错觉”,所以终究无法弄清宇宙的真相。同时,他认为佛法中的“真如”,就是哲学家们所渴望了知的“宇宙万有的真相及本体”,但是亲证“真如”,必须按照佛教的修持方法以“反观自心”。所以,他对佛法与哲学进行了这样的概括:佛法是“从觉化迷”,哲学是“在迷执觉”。
太虚大师在提倡佛法高于哲学的同时,又承认佛学思想中具有与哲学相近之处。他在《唯物唯心唯生哲学与佛学》一文中,认为佛法中的“法性无生”思想与唯物论、“法相缘生”与唯心、法界妙生与唯生非常相似。〔27〕虽然这样的比附非常勉强,但是他毕竟承认佛法中有丰富的哲学思想,可以包融含摄各种哲学。
所以,他在章太炎、蒋维乔等人积极推动佛学哲学化,和杨文会、欧阳竟无等人坚决主张佛法非哲学的同时,表现了一代大师的鲜明态度,无疑具有扬二者之长而克二者之短的合理性。
佛学与哲学的区别是什么????
佛学之精深博大,论理体系之完整究竟,诚为人类文化精华之所在,其对宇宙人生真理之了澈,贯世出世法为一体,实诠哲学理则之极致,而其指论智德之实践,则又处处融汇于吾人生命群体之日常生活中,故远非一般迷信鬼神,徒托空言者之可比,然常人因对之多乏深刻理解,故有视其为仅能存在于知识贫乏之古代社会中,因于人类对自然现象之震撼迷惑,而在宗教情绪与生活之演化中,所形成之一种宗教神学,其与纯论理之哲学,实无所贯通,殊乃一大误解,盖论哲学之目地、价值及功用,在求明析宇宙人生之究竟,而导人类存立于真知至善之境,故其非但批判于文化,且有指导文化之功用,是以论理如不究竟,甚或有所偏失,则虽只一人一家之说,亦往往足以贻误社会人群;今日人类社会之物质文明,故已进入原子太空时代,生活方式亦由原始劳动,进入机械化、自动化之阶段,但在精神方面,则又因为多数人对人生理事之不澈,局于断常偏执之错见,致沈溺于功利自私之深渊,逐物忘心,德性堕落,此实乃二十世纪人类之一大悲剧,而何以导致此人文发展中,智德之不能平衡,吾人实有对人类之知识问题,重新加以反省检讨之必要,而在哲学上迄今仍所未能究竟之根本问题,如宇宙本体之真相,生命理体之究竟,知识能力之扩展等,在佛学上,则早有明确具体之解决,并已有古今千万人之所实证,然而今日之哲学与科学方面,仍未尽将佛学中之全部真理,予以融通运用,此更为人文发展中,一最大损失,故将佛学哲学科学知识之融合应用,以拯救人类社会之陋失、开拓光大人文发展之理路、导人生于真知至善平等自在之理地,实为当世之要务也,笔者孤陋无学,非对某种世学有何成见,存心褒贬,因有感于斯,是乃略抒管见,以供读者指正。
一、对哲学知识之研讨
人类之所以能别于禽兽,组成社会,创造文化,以人为之目地法则,适应改变自然界之因缘制限以善遂其生者,在其自身具有心性上之觉知能力,故论人类知识之所以能成立,主要在能知方面具此心能,其次始为所知方面事物之显现,以意识分别其因果存在中之质量、关系、时空变易等之理奥,故所知之理量,必为能知所决定,而世人在此业果感报之根身器界中,是否真已将其心性之本能全予发挥运用,以创建其正确普遍完整之知识,以供人生之需求,则仍未尽也,古今诸多哲人,于受本身心识能力制限之故,是以其知解,始终只局限于根尘和合妄识变现之现象界,而未能洞澈真如实相之理体,故其论宇宙之本体,则唯心唯物,一元多元之争,历二千余年而未解,在知识论中,理性说、经验说等亦莫衷一是,致使人对社会人生见解处理,陷入一片纷乱中,故常人对人生意义价值究竟为何?多感茫然无所择从之慨!诚堪悲悯之至:谈哲学问题,一般多以为西方哲学较有理序,故即略引西哲数人之学说观之,即可见佛学之穷理究竟矣;在希腊之哲学思想中,首先以哲学解释宇宙之本体者,为泰利士,(Thales.640—548B.C.)以为水乃宇宙之本质,以后接踵之有人认为系大气,又有人言为火,为水火土气,至德谟克利图斯,(Democritus.460—357.B.C.),又以聚离变动之原子释之,苏格拉底(Socrates.460—399.B.C.)对宇宙本体则持存而不究之怀疑态度,然其有言:「余所知者仅一事,乃一无所知。」其对宇宙智德之诠扬,亦仅成为哲学上人本主义之先导;而柏拉图,(Plato.427—347.B.C.),以理念为中心之学,以理念为实有之存在,乃永在变易中万物之理型,亦只乃对苏格拉底之学,作进一步之探求而已;亚里斯多德(Aristotles.384—322.B.C.),虽集希腊哲学之大成,但其以为宇宙乃由质料与形式渗混而成,以为万物之生成有四因,即质料因、形式因、效力因、终极因,此种多因论,又何达因果平等之知,而其全部理则,亦只能作不了义世法之诠解耳,然自亚氏死后,直至中古时期,西方已无第一流有创见之哲学家,多只不过咀嚼模仿前人之思想而已,而经院学派之哲学,立宇宙之第一因归之于一神,是使西方人智能之泉更雕寒矣,以上所引者,故可以当时西方社会,在人文科学各方面之积累体验,尚属幼稚,对人类之知识能力及宇宙人生之探究,尚未能加以反省深入,故虽大哲学家,在论理上仍难免有贸然独断以偏概全之失,即又以近代哲人之知解观之,如理性之代表人物笛卡儿(Descartes.1596—1650.)虽倡以理性推理之说,以窥宇宙之真相,而其所言:「我思故我在」之哲学名言,亦只落唯识学中,第六意识见分之理诠,故其究理,偏止于心物对待之二元;而康德(Kant.1724—1804.)所集创之直观上之时空,悟性上之十二范畴,(量之观念之普遍、特殊、单独;质上观念之肯定、否定、限制;关系观念方面之确然、假定、选择;姿态观念上之疑问、确说、必然。),理性上之三理念,(即藉理性之作用,而以理念为格式,以求统一悟性之所认识。)亦未超心色识用之理限,故彼亦以为人类之所能知者,只为万物之假相,至万物之真相,其称之为「物之自身」者,则不可知;黑格尔(Hegel.1770—1831.),以心色变易之因缘动因为中心,创立正反合矛盾统一之辩证法,其对宇宙理体之极究,亦只能以所谓「绝对精神」之理念了之;而叔本华(Schopenhauer.1788—1860.),则又认为意志乃一切生物之本源,亦为罪恶之渊薮,生命越进化,苦恼亦越增,但意志究属为何?彼亦无以究竟,故成为一极端悲观之哲人;其次如经验派之洛克(Locke.1632—1704.)等之学说,以为知识中之理则,乃由经验而来,则全堕根尘识用之网中矣,另有以罗素(B.Russell.1872—)为代表之新实在论者之哲学,不过在知觉中承认物质之存在,在思想中承认逻辑之存在,其要点以为论知识,该向外求,不应反身自省,故以为现象界,仅系一连串之事素而已,其知解离心性本觉大用之理事一如理体远矣!至于近代唯物论者之学说,如霍布士(Hobbes.1588—1679.),其机械之运动说,何尔巴哈(Holbach.1723—1789.)之物质与运动说,布什纳(Buchner.1824—1899.)之力与物统一说,皆只是视为常识上或自然科学上之见解,以心为物,因果颠倒,断常偏执之失大矣,他如马克思(K.Marx.1818—1883.)以矛盾为中心之辩证唯物论,则更不足将其视为哲学一谈矣,罗素曾言:「西方之文明,将不免随其文明所生之战乱同归于尽。」此语竟出自当代西方之大哲学家之口,殊足令一般世人深省,由以上西方诸位哲人之知解中,可得一明确之认识,即无论哲学上之形式论理,辩证论理,实验论理,其理解皆不出佛学中,八识变用之理量范畴,如以之为已究竟人生之理奥则仍未也,故以今日之人类知识贫乏尚有待知力之解放,以扩展其领域,则未为言之过早也。
二、佛学对宇宙人生之究竟
一般宗教思想之产生发展,故有其历史社会之缘素,以作其教化因缘之统合。但佛学之中心义理,全系由释迦牟尼佛,以其亲所悟证宇宙人生之真理,而宣化于世间者,故其圣言量,乃顿超人文知识之积累,究竟了义之理则,此为佛学异于其它宗教思想与哲学之特点所在。其所论及宇宙生命实相理体之真如奥义部份,因非未明心见性之常人心识量,所能达其理奥,本文暂不申论。其次之融通于世间法者,如心物一元,体用如如之本体论,唯识变现,缘生无性之知识论,内明本觉,体全用中之方法论,众生平等,物我一体之社会观,生死一如,无我为人之人生观,慈悲普度,智德合一之道德观,解行相应,理事一如之实践论…等,皆为剖示宇宙指导人生之理则。而佛学从根本上,即揭弃一般宗教玄学之虚无主义,及独断迷信之教条主义;以佛性本来平等,是以众生皆可成佛,真如本际三身四智之性德功用自在,非乌托邦之玄想故,人皆可得实证。为非令人迷信鬼神,崇拜偶像故,信解行证,其六度万行,皆有具体之科学实践方法。佛出人世间,不离世间觉,全知、全能、永恒、自在,身心性德之理量同于虚空,空有一如,法法平等,处处化人间为极乐,拔众于苦海,焉能谓佛学与现实人生脱节。其无我为人,舍身救世,无相布施之菩萨行,更为促进人类助与社会进化之精神动力,是故如人皆能以佛学为生活实践之旨归,则人生社会,自趋于和乐善生之大同世界矣!故论知识之真理标准,唯佛学足当之也。
三、禅学对人类知力之解救
佛学中之禅学,亦可视为全体生命智力解救之学,旨在使每一生命之个体,均自愚痴沉沦中解脱,同证无上正等正觉之理体,其在理事上,又诠全部佛学世学之理奥,故又非语言文字之可诠述。今仅于其无量义中,略谈其一,盖欲解决人类在知识方法上,所受能知方而知力之制限,禅学中悟证之「内明直觉」,实乃最精简直捷之科学方法。但其与哲学家所提倡之理性直觉诡异,盖所谓理性直觉,仍只以意识功用之理念,作为推理判断之主题;而「内明直觉」,则为转识成智之功用,使心性智德之本能,全予发挥大用。盖心体本净,量同虚空,知穷万法;心之不明,为惑所蔽,如镜去尘,照物即真矣!内明初觉,则洞达现象界因缘事理;内明二转,则六根互用,直达本体界生命之真如理体;内明三转,则心色一如,平等自在;内明同转,心性能用与宇宙之理量合一矣!然则一觉已尽,又何言门,此乃理虽顿悟,事须渐修之方便也。有人或致误会,以为此乃不科学之玄谈,佛学乃哲学之哲学,亦乃科学之科学。对佛学稍具常识之人,皆知在佛学经论中,甚多自然科学之先验,而深证者则更可窥见,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理奥尽诠其中。而对「内明直觉」之修学,由起行至证用,即仅论其皮毛之表德功能方法等,与今日之生理学、原子学、电学等科学皆可相资印证。某教授(非佛教徒)曾以古今学佛之人甚多,而证道者却日少,思惟方法太难,且非人皆可行可证,以疑问于笔者,事实上本简而易行,人皆可证,只在信行之诚笃与方法之当否而已。至于有关「内明直觉」修行之理径,五十一年八月份及十一月份之台湾佛教月刊中,笔者曾有「谈禅」及「谈唯心识定之修行理路」二文论及。但以笔者之体验,在理则上虽一,而方法上则又应依修学者之主客观因缘条件而决定。佛法本应缘宣化,八万四千以至无量法门本无一法之可执也。今日人类之追求知识,正同一群以巾蒙面之人,迷困于森林之中,摸索、困惑、争辩不休,欲辨明外境之究竟,以求出离善遂其生而不可得,只知向外一步步之摸索前进而不知向内自求,去面巾相,其愚执何甚!谚云:「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」心性之功能乃一切知识本源之根本工具。「内明直觉」正乃扯去人类知力所为制阻之面巾之法。其修之法,理不碍事,事不碍理,男女老少,在家出家,行住坐卧,皆可修行。一旦悟证,则能尽心性之用,亦即穷万物之理矣!与宇宙合一之大自在理体,本来如是;至将佛学哲学科学之知识,予以彻底之融合运用,以济人类之困厄,则更急待社会人士之共同努力也。
以上就是大学路小编整理的内容,想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内容敬请关注大学路。

 全面禁止课外辅导机构?别误解了,要整顿的是这类培训班
全面禁止课外辅导机构?别误解了,要整顿的是这类培训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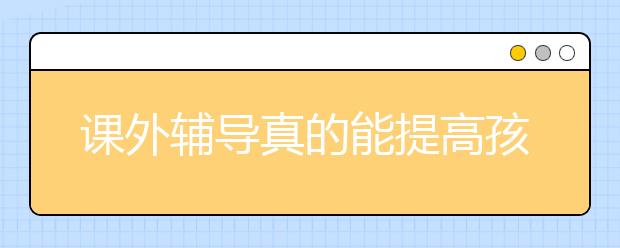 课外辅导真的能提高孩子高考成绩吗?
课外辅导真的能提高孩子高考成绩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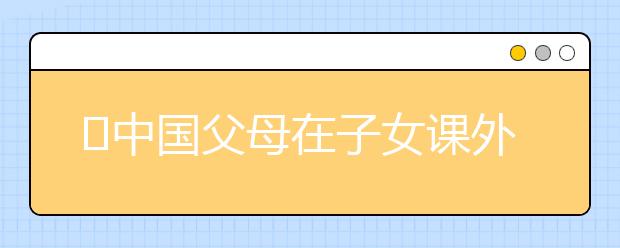 中国父母在子女课外辅导上花了多少钱
中国父母在子女课外辅导上花了多少钱
 全面禁止课外辅导机构,你支持吗?
全面禁止课外辅导机构,你支持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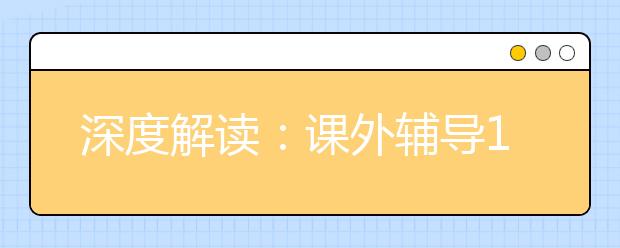 深度解读:课外辅导1对1,在线课,小班课,大班课,家长该如何选择?
深度解读:课外辅导1对1,在线课,小班课,大班课,家长该如何选择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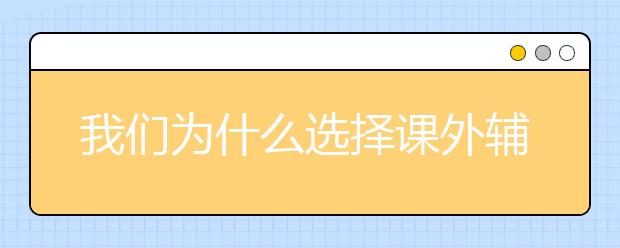 我们为什么选择课外辅导?
我们为什么选择课外辅导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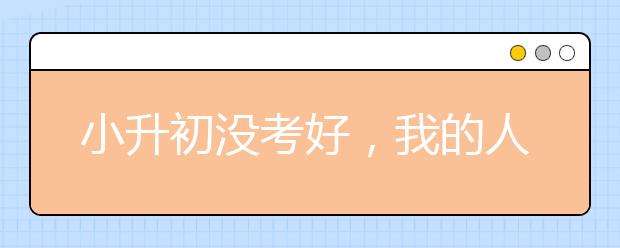 小升初没考好,我的人生好像完蛋了
小升初没考好,我的人生好像完蛋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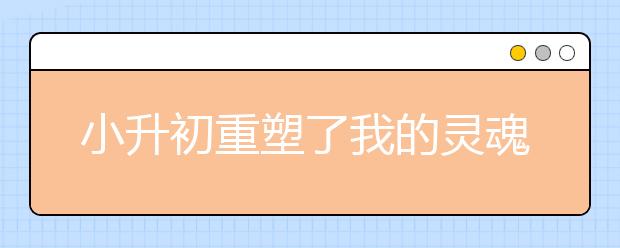 小升初重塑了我的灵魂,还有肉体
小升初重塑了我的灵魂,还有肉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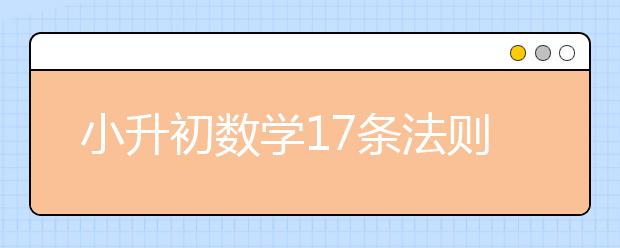 小升初数学17条法则,做题一定会用到!
小升初数学17条法则,做题一定会用到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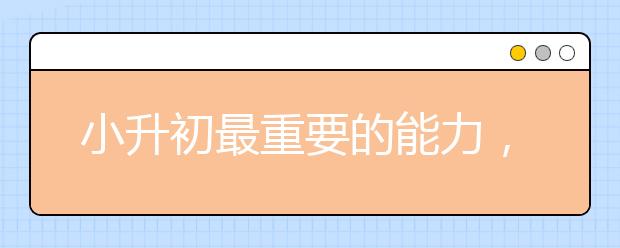 小升初最重要的能力,现在开始准备一点也不晚!
小升初最重要的能力,现在开始准备一点也不晚!